 第五十四章 夢魘(26)-蠱惑 荒誕推演遊戲
第五十四章 夢魘(26)-蠱惑 荒誕推演遊戲
 第五十四章 夢魘(26)-蠱惑 荒誕推演遊戲
第五十四章 夢魘(26)-蠱惑 荒誕推演遊戲
「老、師?」
伶人放慢速度,用一種似笑非笑的語氣重複了一遍,眼中神色晦暗不明。
過了兩三秒,他斂住嘴角的笑容,只留下淡淡一抹,讓人看不出情緒:「真是意外,從前你也沒有用這個稱呼過我,讓我有些……受寵若驚呢?」
他伸出一隻手,似乎想揉一揉虞幸的頭髮。
放在直播間觀眾的眼裡,這兩人的舉動怎麼看都太詭異了些,說針鋒相對吧,光看動作,好像又有一種習慣性的、十分靠近的社交距離,這代表著雙方都曾經允許對方的接近。
可若是說兩人之間是友好的……那恐怕是眼瞎了。
存在於雙方之間的惡意和警惕,即使是完美無缺的笑容都無法掩飾,更別說,剛才幸就像藉助鑰匙環的禁錮給伶人來一刀。
那可是照著脖子抹的,一點都沒留情。
「能教會我東西的,稱一聲老師不過分吧?」虞幸笑著反問,順勢悄悄後退了一步,不著痕跡讓過了伶人的手,指尖的攝青夢境輕巧打了個轉,又倏爾固定住。
寒光映照著伶人的手指,無疑是在宣告,如果再想做這種動作,匕首刃會毫不猶豫地削上去。
與武器上傳來的冷硬不同,虞幸的語氣就好似見到了一個親近長輩一般:「你教給我的,我很喜歡。」
「呵,這麼多年,長進不少。」伶人看著他熟練的握匕首姿勢,還有消失於眼中的恨意與癲狂,真心實意誇讚了一句。
「其實沒什麼長進,我這個人很笨的。」虞幸笑道,然後主動伸出一隻手,朝伶人腰上的布料摸去,「咦?這裡怎麼有個破口?」
伶人目光微微下垂,任由那隻看起來十分無害的手探到破口處,好奇似的將幾層衣服往兩邊撥了撥,那人還仿佛並不知情地問:「邊緣口很平整,是被利器劃開的吧。唔,沒有傷口,看來猜錯了。」
「嗤。」伶人忍不住發出一聲帶著真切笑意的音節,這是虞幸那位隊友,趙一酒的祭品短刀刺中的地方。
虞幸還真是,學了他很多東西。
尤其是在睜眼說瞎話和找准角度氣人這方面,一邊嘲諷氣人,一邊還能試探到他的情況。
「你沒看錯,傷口已經恢復了。」他擋住虞幸試圖往他腰間掛著的小布袋處伸的手,輕笑一聲,「我說的都是真心話,許久不見,你進步了很多。」
在虞幸目光多往布袋子那裡停留了一秒之後,他補充道:「你性格的成長方向,有些出乎我的意料呢,看來,我對你的關注還不夠,否則也不會被你找到方法進入荒誕之後才找到你。」
「嗯哼,我也是想了很久,才發現途徑的。」虞幸偏頭望他,「不過,你確定要用這么正經的語氣和我說話?比起教我唱戲時候的你,我還是更喜歡……在火中嘲諷我的你呢。」
「那多沒意思,再說,你也不是當初那個嘲諷兩句就要哭的小孩子了。」伶人微笑著,露出有些懷念的神色。
他們都知道,現在他們提起的,是那場撕破了一切偽裝的大火。
受害者已經可以心平氣和地主動提出這件事,而兇手,則不以為意的將當時虞幸的絕望歸結於「嘲諷幾句就要哭」,似乎在他們心中,那場大火已經被模糊和淡忘了。
可,這不可能。
他們都只是在用彼此之間矛盾的起始當作試探對方的工具而已。
虞幸握緊匕首,目光漸漸產生了些變化。
伶人也站在原地,等著他時隔多年的,不那么小兒科的進攻。
感情好的偽裝玩一會兒就夠了,他清楚,既然過去的種種屈辱沒有完全磨掉虞幸骨子裡的驕傲,那這種殘存的驕傲就不會允許虞幸一直對他笑臉相迎。
雖然……他還是很喜歡看起來很乖的虞幸就是了。
反正虞幸已經成為了推演者,如果可以的話,他會讓虞幸……進入單稜鏡,回到他的身邊。
無論是徹底墮落,思維扭曲不再在意過去,還是抱著一身怨氣蟄伏在他身邊找機會永遠地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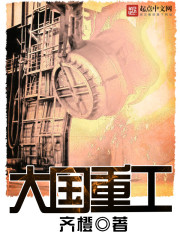 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、礦山裝備、電力裝備、海工裝備……一個泱泱大國,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。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,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,用汗水和智慧,鑄就大國重工
大國重工 冶金裝備、礦山裝備、電力裝備、海工裝備……一個泱泱大國,不能沒有自己的重型裝備工業。 國家重大裝備辦處長馮嘯辰穿越到了1980年,看他如何與同代人一道,用汗水和智慧,鑄就大國重工
 系統供應商 被廢材逆襲,你是否屈辱? 成為天才的墊腳石,你是否悲憤? 身為出場兩集就掛的炮灰,你是否不甘? 不用擔心,一切有我! 身為諸天萬界唯一的系統供應商,我可以為你量身定製各種隨身系統,讓你
系統供應商 被廢材逆襲,你是否屈辱? 成為天才的墊腳石,你是否悲憤? 身為出場兩集就掛的炮灰,你是否不甘? 不用擔心,一切有我! 身為諸天萬界唯一的系統供應商,我可以為你量身定製各種隨身系統,讓你 進化終點 銀河系聯邦憲歷年,太陽系紅日帝國即將迎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——年獨立紀念日! 而在遙遠的紅日帝國邊緣的海王星馬杜爾開採公司的一個礦坑裡,一個厭惡合成食物的歲少年正在追逐一隻少見的野兔,孰不
進化終點 銀河系聯邦憲歷年,太陽系紅日帝國即將迎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——年獨立紀念日! 而在遙遠的紅日帝國邊緣的海王星馬杜爾開採公司的一個礦坑裡,一個厭惡合成食物的歲少年正在追逐一隻少見的野兔,孰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