 卷五 第769章 長樂的情理法 貞觀無太子
卷五 第769章 長樂的情理法 貞觀無太子
 卷五 第769章 長樂的情理法 貞觀無太子
卷五 第769章 長樂的情理法 貞觀無太子
「你沒說錯,法治自然要以法為重,這沒毛病,哪怕是鬧到我兄長那裡,他也挑不出個理來。」長樂想了想了,說道,「但在施行法治之前,最重要的卻不是法治,而是我們之前提到的三公,即公平、公開、公正。
這是老百姓信服我們所謂法治的前提,能理解麼?」
「不是,當我們就律法頒布下去,老百姓難道還敢不信服不成?」武媚有些費解。
她出生在大唐,而且還是公侯之家,自小聽聞和見識的便是如此,所以長樂她們說的那些,她真的不懂。
「這是大明,不是大唐,知道麼?」琢磨了一番,長樂說道,「大唐可以用你說的那一套,畢竟在那裡,啥都講個恩出於上,用兄長的話來說,在大唐,更遵循聖人之言『民可使由之,不可使知之』但在大明不是這樣的。
因為大明起家於微末之際,加之之前姚小胖說的,大明成分問題,所以大明從一開始,就很注重讓老百姓知道我們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。
沒辦法,當時大明別說兵力,就算人口也只有數百之眾,借著日月山,硬撼慕容順數萬鐵騎。
那個時候,不給他們解釋清楚,他們很難看到希望。
而當時日月山,哪怕只有數百人,但組成之複雜,你可能都不敢想。
在那個節骨眼兒上,公平、公正、公開,就顯得極為有必要。
而最後哪怕我們拿下了慕容順,甚至一舉占領了赤水源,但後面幾年,我大明也是連年大戰,這個習慣也就被保留了下來。
現在,大家其實都習慣了,不單單是百姓,就連朝廷也習慣了。
所以,法治的保障,便是三公,這麼說,你能明白麼?」
其實長樂也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,反正她就是想到了什麼就說什麼,至於武媚能不能領會,那就不是她的問題了。
好在武媚天生就聰明,而且與生俱來有著從政的條件,一聽長樂這麼解釋,多多少少還是明白了其中的關鍵,這才說道:「這也不衝突,但法治的最後,還得是法,我們是不是得先從這個為突破口呢?
是以重典治國,還是以孝為本?又或者是以什麼別的?
這法治,總得有個跟腳步是?」
「不,你搞錯了。」長樂搖了搖頭,說道,「法治,就是以法治國,如果硬要給它加點兒什麼東西的話,也只能是情、理、法。
但法一定是最重要的!」
情理法?
聽長樂這麼說,眾人一時都有些無言。
他們也不知道,長樂其實早就有了一個粗略的想法。
甚至可以說有了一個以法治國的輪廓。
只是她年紀不大,加之能力確實有限,無法將其具象化。
這會兒眾人聽到了她法治的核心,當即就有人問道:「情理法,法我能理解,但情和理各代表什麼?」
「之前我考慮過,以孝治國,雖然不可取,但也並非沒有可取之處。」長樂想了想,這才繼續說道,「情,便是取的以孝治國的可取之處。
比如,有人侮辱了某一人的父母,作為子女,他該怎麼做,能怎麼做?律法又支持他怎麼做?
這需要一個詳細的準繩來給每一個人答案。
這就是情。
這也是之前兄長一直念叨的,法理不外乎人情。
至於理,那就很簡單了,單純就是道理。
正所謂,理不辯不明,所以,我們允許任何未被大明律法判定為有罪之身的人,進行有罪或無罪辯護。
因為在大明律法判定之前,他本身就是無罪之身,是應該享有我大明百姓,基本擁有的權利的。
這不是誰賦予他的,這是他作為大明百姓,與生俱來就擁有的權利。
這便是理,可以辨證,也可以避免真有人冤死在我大明的監牢之中,更能在不斷的辨證之中,完善我大明的律法。
至於法,那就是最後的準繩,是衡量一切罪惡與善良的標尺。
 位面成神之虛空戒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,佛說『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。』辛寒說『三千大千世界裡都有我!』 佛說『你厲害,我服!』感謝起點論壇封面組提供封面!新書《位面之狩獵萬界》已發布,求收藏,求
位面成神之虛空戒 一花一世界一葉一菩提,佛說『一粒沙里有三千大千世界。』辛寒說『三千大千世界裡都有我!』 佛說『你厲害,我服!』感謝起點論壇封面組提供封面!新書《位面之狩獵萬界》已發布,求收藏,求 九星毒奶 這是一個充滿了星力的平行世界。星圖、星技、星寵、覺醒者大行其道。魂穿而來的江曉,體內蘊含着一張奇特的內視星圖,成為一名稀有的醫療系覺醒者。他本想成為一隻快樂的大奶,但卻被眾人冠上了毒奶之名。這
九星毒奶 這是一個充滿了星力的平行世界。星圖、星技、星寵、覺醒者大行其道。魂穿而來的江曉,體內蘊含着一張奇特的內視星圖,成為一名稀有的醫療系覺醒者。他本想成為一隻快樂的大奶,但卻被眾人冠上了毒奶之名。這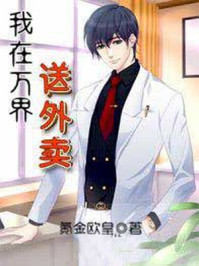 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
我在萬界送外賣 內容簡介:葉晨八歲那年,算命老道說:你十八歲那年將黃袍加身,天天山珍海味為伴!我信你個鬼你這糟老頭子!外賣員的黃顏色工作服也是黃袍加身?結果葉晨果真成了黃袍加身魚肉為伴的外賣員,不過……他的外